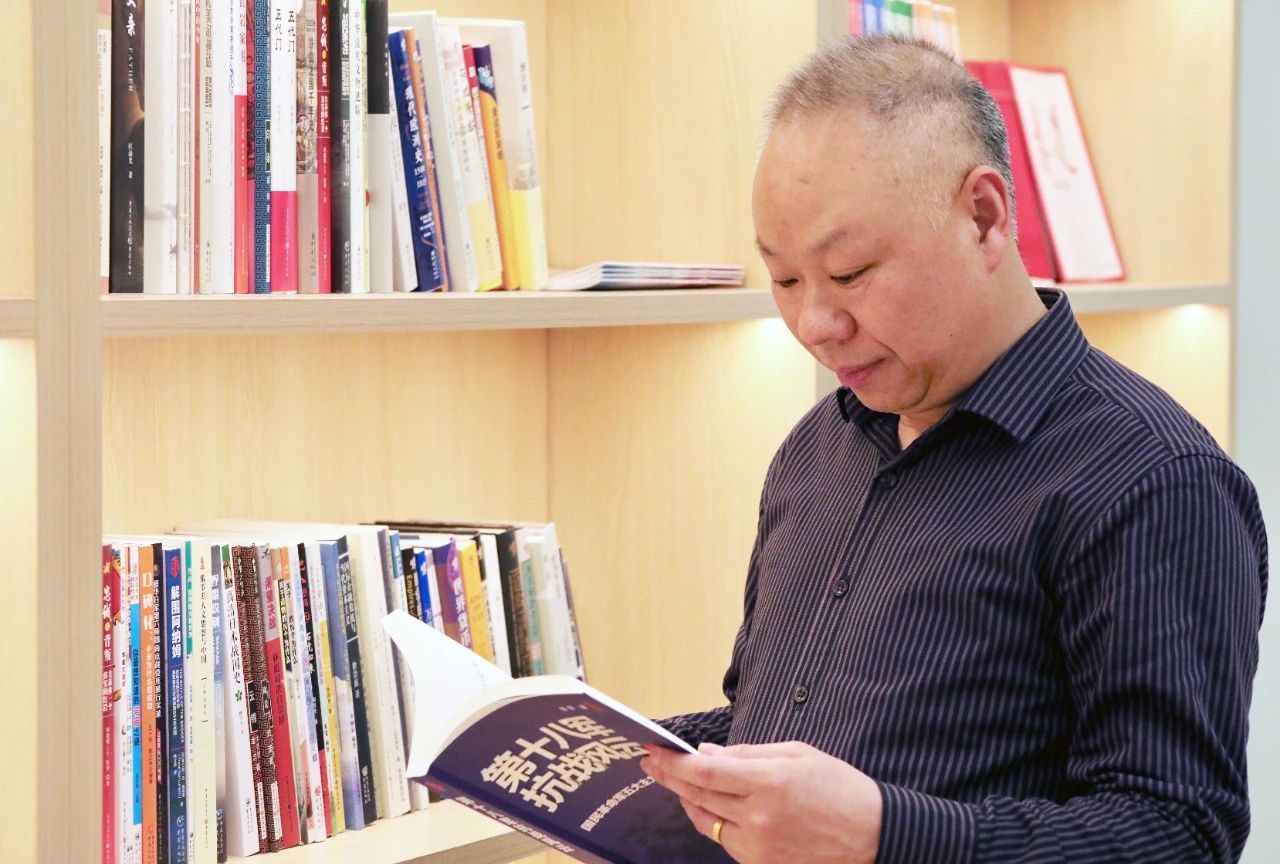父亲的身影,是重庆市万州分水中学援藏教师陈云成长过程中的一座灯塔。父亲戍边西藏的岁月虽少在他的面前言及,却早已在少年陈云的心中埋下了一颗向往的种子。中师时,他梦想追随父亲的足迹,一身戎装,守卫边疆。命运虽未成全他的军旅梦,但对这片雪域高原的渴望,却如暗河潜流,从未停息。
2016年,命运为陈云开启了另一扇通往西藏的门——他以教育援藏的身份,终于踏上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,循着父亲的脚印,开启了为西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的征程。
初临的挑战与心灵的叩击
初到昌都,多变的气候、恼人的高原反应、挥之不去的感冒,曾让陈云的身体经受着重重考验,心生犹豫。更大的鸿沟是语言。与学生、家长交流的阻滞,让他的教学工作举步维艰。
然而,一次偶然的搭车经历,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。那天,错过校车的陈云,焦急中搭上了一位藏族老乡的顺风车。交谈中,老乡的话语里满是感激与质朴的期盼:“我家孩子真有福气,遇上你们援藏老师!数学老师讲得清楚,孩子进步可大了。要是早几年有你们,我女儿肯定更有出息!”得知援藏期限三年,老乡的笑容瞬间凝固,忧心忡忡:“三年后你们走了,我小儿子才初一,那可怎么办啊?”陈云连忙解释会有新老师接替。老乡这才稍稍宽心,喃喃低语:“要是你们能一直教下去,彼此熟悉,娃娃的学习才更稳当啊……”
这番对话,如同一束光,瞬间穿透重重阴霾,驱散了陈云所有的犹豫与阴郁。那一刻,他无比确信——援藏,是此生最正确的决定!他的存在,对这片土地上的孩子,意义非凡。
家访的记忆与千钧的托付
2019年盛夏,陈云攥着第二次援藏申请表的手微微发颤。脑海中,达普村家访的情景清晰如昨日——那是参加“六个一”活动时,他与6位援藏教师走进学生蔡巴拉姆家的场景。
在卡若区城关镇达普村蜿蜒山路的尽头,低矮的木屋升起袅袅炊烟。推开门,孩子爷爷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瞬间绽开笑容,用生硬的汉语不断重复着“老师好”,布满老茧的双手急切地将刚烤好的饼子塞进老师们手里。年轻的母亲则默默提着酥油茶壶,目光紧紧追随着老师们的茶杯,只要见浅了一点,便立刻上前添满,生怕怠慢了一丝一毫。
屋外,细碎的脚步声徐徐传来。几个周末放学的孩子悄悄聚在门口,踮着脚尖,向屋内张望。他们的小脸被高原的风吹得通红,衣衫虽旧,有的还打着补丁,但望向陈云他们的眼神,却纯净而炽热。
临走时,爷爷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恳求。“老师,娃娃们就靠你们了。”粗糙的手掌紧紧握住陈云的手。陈云知道,这双在高原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手,如今把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全部希望,都郑重地托付给了这群远道而来的老师。那一刻,他明白,孩子们眼中那沉甸甸的信任与期待,他无法拒绝,更无法辜负。
女儿的抉择与艰难的成全
当第三次援藏申请摆在面前时,陈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。书桌上,申请表、工作简报、学生们写的“最美援藏教师”征文文集堆在一起。他枯坐良久,难以下笔。试探着向妻子提起,妻子沉默半晌,轻声说:“你先问问女儿吧,她同意,我就没意见。”
女儿放学看到申请表,不解地问:“爸爸,为什么还要去?”望着即将升入高中的女儿,陈云心中涌起深深的愧疚。他已经错过了女儿6年宝贵的成长时光,难道还要再错过关键的3年吗?面对女儿严肃的追问,西藏孩子们那一张张黝黑、带着高原红的小脸,那一双双充满对知识渴望的清澈眼眸,瞬间清晰地浮现眼前。“爸爸舍不得这届学生,”他声音不高,却异常坚定,“那里的孩子……更需要我们。我想带他们走出大山,去看更广阔的世界。”
一边是至亲骨肉,一边是雪域学子,天平的两端都重逾千斤。最终,是女儿的理解和支持,让这个坚强的男人瞬间热泪盈眶。“我去昌都看过你。”女儿轻声说,“我知道你的学生,看过他们写给你的纸条和信,知道他们都喊你‘陈爸爸’……比起我,他们,更需要你。”
九载的执着与深深的不舍
9年时光,悄然滑过指尖。陈云在高原播撒的心血,已然结出累累硕果。曾经坐在他课堂上的孩子们,如今已在各自的天空绽放光芒:有人披上圣洁的白衣,成为高原医院里的守护者,为乡亲们的健康保驾护航;有人执起粉笔,站在三尺讲台,像他们的“陈爸爸”一样,点燃更多孩子心中的希望之火;有人扎根基层,用智慧和汗水,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……
今年是陈云第三次援藏的最后一年。记者找到他时,他正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做着最后的整理。抽屉的最深处,静静躺着一张援藏申请表的复印件——正式的表格早已上交组织,结果尚在未知。
看着这些承载着无数回忆的物件,陈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不久,他就要返回重庆。这一次,他要利用高三毕业后的这个长假,好好陪伴即将步入高三的女儿。
或许不久,陈云会带着新的使命,重返这片牵动他灵魂的雪域;又或许,他将把这份长久的牵挂,化作对女儿更深沉的陪伴。无论前路如何,他倾注于这片高原的深情,早已化作春风细雨,滋润着万千心田。